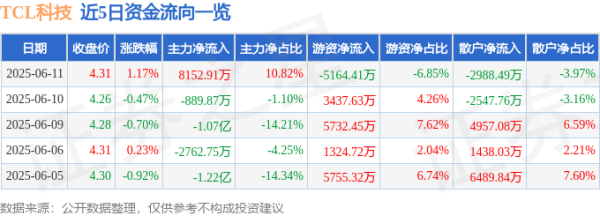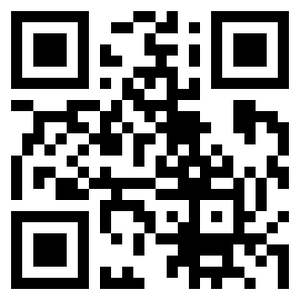“1933年2月的一个雨夜,你真的不动心?”看守眯起眼,在狱门口小声嘀咕。陈赓卷着破棉衣,声音不高却掷地有声:“再回上海,我就带十万兄弟一块来。”短短一句话,像雨点打在铁门上优配速至,发出清脆回响。
往前推四个月,陈赓的右腿还是一条血肉模糊的伤口。1932年秋,他率红四方面军第十二师死守扶持山寨,误中一颗7.9毫米子弹,小腿骨裂,医务班找不到手术锯,只能草草包扎。看似结痂,其实碎骨未取,感染反复,疼得钻心。要命的是他连马都骑不了,部队机动作战时,陈赓只能咬牙蹬着拐杖。

深秋清晨,他把拐杖“咚”地插进泥土,对张国焘支吾出的“当四方面军参谋长”客气笑笑:“参谋长要能骑马,我掉队了。”随身只带一本《孙子》。这一走,他准备直奔上海。既为治伤,也想暂离张的权谋氛围。
到上海后,他把身份压在胸口,只对骨科名医牛惠霖说自己是“码头扛包时骨折”。牛医生却一眼识破弹道痕迹,拍拍桌子:“别解释,我懂。医药费,这回算我支持抗日。”陈赓坚持留下几根金条优配速至,塞进医馆抽屉。试想一下,一个全身绑着石膏的红军师长,躲在十里洋场弄堂里,同鲁迅讨论军事形势,夜里还要烧开水给腿伤消毒,上海滩的灯火因此显得格外讽刺。
有意思的是,他并没忘工作。住院那几周,中央特科送来空白蜡纸,陈赓手绘鄂豫皖态势图,重点圈出张国焘的布防漏洞。后来这张草图被上海鲁迅纪念馆珍藏。

1933年3月,腿骨基本愈合。中央让他火速赶赴瑞金参加部署。他拄着新木杖,在丽都大戏院门口偶遇昔日特科同事——此人已转投军统。对方一个眼神,帮派巡捕蜂拥而至。陈赓腿脚未稳,终被拖进公共租界巡捕房。
消息很快漂到南京,蒋介石皱着眉:黄埔三期第一名、自己当年在广州东征的救命恩人,如今落网,杀不杀?蒋夜半列了三条:恩人不能杀,黄埔旗帜不能凉,红军里的黄埔生还得留个联络点。彼时宋庆龄、蔡元培、何香凝等也在奔走求情。看似人道优配速至,实则各怀算盘。
拘留所半地下室里,廖仲恺之子廖承志递来半截香烟。“咱俩身份,谁也别多说,就说援东北义勇军。”陈赓点头,转身对着铁窗大唱《国际歌》。他知道墙外有人在听,那是给同志、也给敌人看的态度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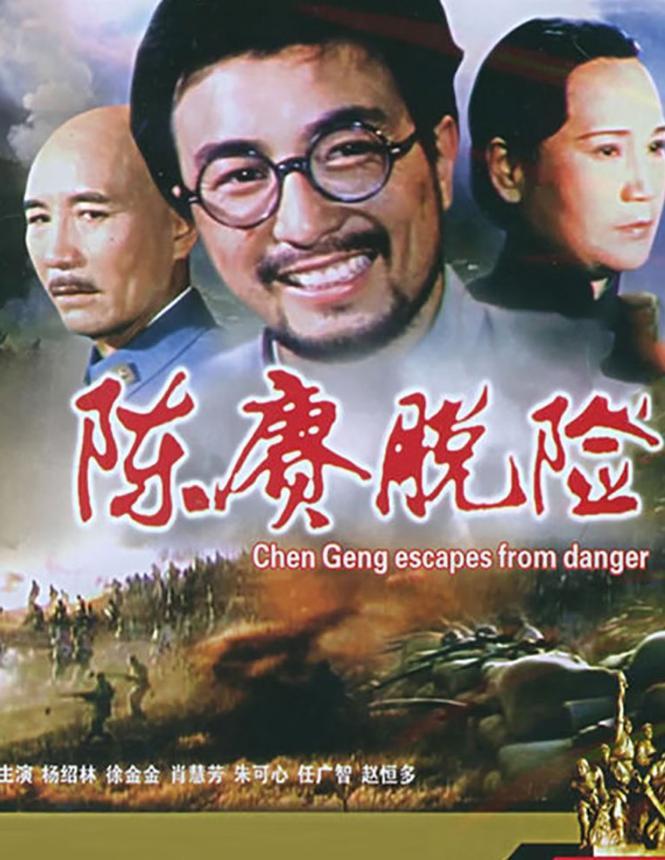
审讯室灯泡忽明忽暗。顾顺章敲桌子:“老同学,跟着委员长,好处多得很。”陈赓笑得云淡风轻:“我信马列,不信美金。”蒋介石亲自登场时,话说得更温和:“欢迎你改弦更张,哪天再回南京,我还替你摆接风席。”陈赓抬手行了个黄埔军礼:“校长放心,再来,我带十万部队来赴宴。”蒋一时语塞,放人也不是,不放人也不是。
压力越滚越大。四月,南京政府以“保释候审”名义把陈赓放到公共租界“居住”。表面宽宥,暗中跟了两层便衣。陈赓借口复诊,摸清盯梢习惯后,一夜消失。几经辗转,他从沪闸火车站混上货列,到江西瑞金时,腿伤仍隐隐作痛,却已站在作战会议室门口。
后面的故事波澜壮阔。抗战全面爆发,他奔赴太行,指挥晋冀豫抗日根据地;解放战争中,他入东北打四平,急行军千里奔袭大同。在东北野战军里,不少骨干正是当年黄埔学生和旧部,他们悄悄说:“老校长要是知道咱有几万人,得后悔当年没把你关死。”陈赓摆手:“做事别记私仇,记大仇。”

1949年5月22日凌晨,南昌城头炮火连天。解放军第三兵团以三个军外加特种兵,共十一万余人强渡赣江。陈赓站在指挥所,身后挂着江西简图,腿伤遇雨仍隐隐作疼。城破后,他让通信兵打出无线电口令:“南京说的‘再回来’,今天我履约了。”
不少研究者后来总结,蒋介石当初放走陈赓,是“以小恩换大计”,可这依旧是一笔赔本买卖。政治算计挡不住信仰力量,也无法阻挡历史进程。当年半地下室里的那句硬气回应,被陈赓用一座省会、十一万部队兑现得干干净净。
迎客松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