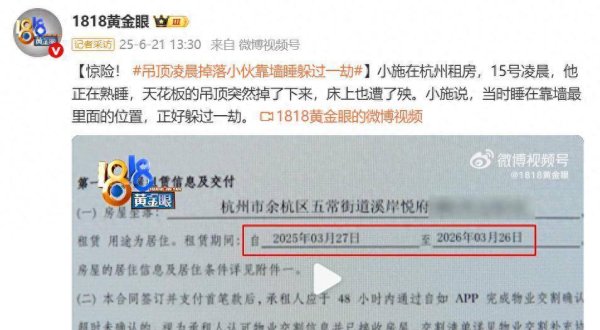“1997年11月12日上午十点,北京东四一间简朴会议室里,我不同意!”八十三岁的杨成武抬手砸了砸桌沿联丰配资,声音不高,却把窗外的寒风都震住了。坐在对面的几位部门负责人与老厂长沉默片刻,有人轻声答道:“杨老,总量控制压力大……”他摆摆手:“再难,也不能把几十年的老工人撂在路边。”

那一年,国企减员增效进入加速期,几百万人拿着一张红印信封离开熟悉的车间。新闻里喊着“市场倒逼改革”,可在杨成武眼里,工人不是统计口径,而是跟他一起扛过枪、修过飞机跑道、支前送粮的“自己人”。旁边有人提醒他已退休多年,不必操这份心,他眯着眼回答:“离岗不离人民。”
熟悉杨成武的人都知道联丰配资,他说这句话不是姿态,而是信条。1914年腊月,他出生在福建长汀县一个佃农家,冬天的菜窖里只剩一把霜打白菜,却硬是啃着旧书学字。十六岁参加闽西暴动,他在祠堂口对乡亲说:“翻身不靠等,得自己闯。”那股子“闯劲”把他一路推到工农红军第四团。
1935年5月,大渡河水如沸。杨成武、黄开湘率红四团沿山崖奔泸定桥。雨夜里脱鞋塞怀,脚板被碎石划得血迹斑斑,他回头吼:“有一个掉队,全团脸上无光。”桥板被敌人拆得只剩铁链,二十二名突击队员攀索前进——火舌漫桥,河水轰鸣。两个小时后,红旗插上西岸。杨成武数人头,只剩下自己和十几名轻伤兵。他没掉泪,把军帽摘下,低声说:“记住,他们是为老百姓死的。”

五十一年后联丰配资,也就是1986年长征胜利纪念日,他回到泸定。江面风平浪静,桥板已换成坚固木梁,他倚栏默默良久,自言自语:“战友,你们要是看见今天的日子,心里该踏实了吧?”陪同的县干部记得,他那天中午什么都没吃,只在纸上写下八个字:不弃群众,不负牺牲。
这种执念,被他带到了九十年代。改革是阵痛,他承认;可当旧车间关灯、汽笛停响,他举例:“红军长征,最难时也要把老百姓带上。现在怎么能把工人撂下?”在那场专题座谈上,他建议三件事:其一,设立再就业基金,由盈利央企按比例捐助;其二,保留最基本的医疗、住房配给;其三,动员老技术骨干建师徒传帮带中心,“别让几十年手艺烂在抽屉里”。有人以“预算不足”婉拒,他抬头加重语气:“当年运枪,没子弹也得上!”

会后,他把自己每月的离休金一分不少全投进“安置困难职工互助会”。家人担忧,老将军笑道:“我还能吃几碗饭?”报纸没有大篇报道,但下岗工人私下传着:“杨老真够意思。”
时间来到1998年春,多地出现首批再就业服务中心,第一笔启动资金里,能查到杨成武和几位老兵的汇款记录。成效并不完美,可至少开了个头。那年盛夏,东北一家老厂的技师马明辉给他写信:“多亏那间中心,我又进了维修队。”短短几行字,老将军读了三遍,把信叠得整整齐齐放进抽屉。
2004年2月14日清晨,他在解放军总医院安静地闭上眼睛,桌上那只旧皮箱仍放着“互助会”收据。告别仪式那天,细雪不停地落,排队的人从西长安街拐到阜成门。有人说:“他是大将军。”也有人说:“他是给我们说话的人。”陆军某师的中年军官朝灵柩敬礼后轻声嘟囔:“工人不能自生自灭——我记住了。”

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,工厂的汽笛声却仍在新时代的街角回荡。那些被他惦念的工人、农民、战士,才是他一生最深的牵挂。杨成武用八十九年的脚步告诉后人:不管风浪多急,把人民装在心里,才能站得稳,也走得远。
迎客松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